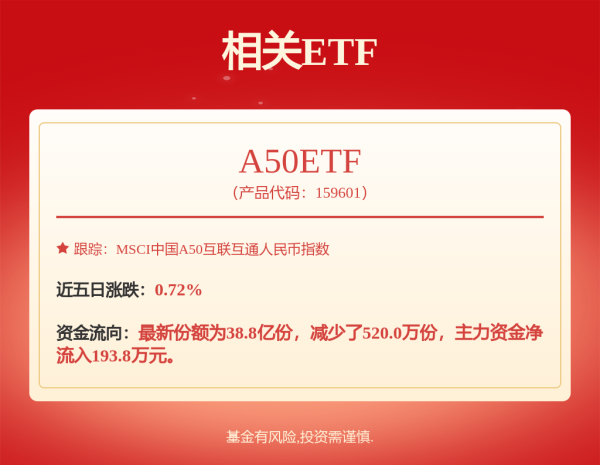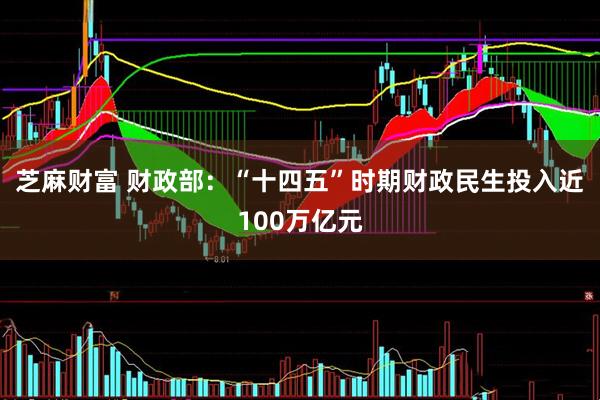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富途证券
范仲淹的厉害,从来不是靠嘴说出来的,他靠的是断齑画粥、为民请命、戍边抗敌、力推新政,一步一步杀出来的本事。
他不靠血统、没有后台,全凭一身骨头硬撑起大宋脊梁。毛泽东亲口称他“文武双全”,刘少奇引用他“先忧后乐”训诫党员。一个宋朝人,凭什么让共产党人铭记数十年?
困顿中成长,苦读铸品格苏州的老范家,在宋代算得上显赫,范仲淹一出生,父亲是节度使,有权有兵,是地方大员。结果不到一岁,父亲突然去世,整个范家冷得像块冰。亲族毫不犹豫,把孤儿寡母赶出了范氏族宅,连门都不让进。
母亲谢氏没办法,只能改嫁一个苏州推官朱文翰。从那一刻起,范仲淹连姓都被换掉了,成了“朱说”。
展开剩余89%他小时候不懂这些道理,只知道自己比别的孩子吃得差、穿得破。四岁搬到山东长山县后,生活没好过一天。村里人都知道这个小孩怪得很,别人玩,他读书;别人吃,他饿肚子。
最狠的,是二十一岁那三年。他跑到淄州的醴泉寺去读书,穷得只能煮一锅稀饭,用腌菜拌着吃。一锅分成四份,早晚各吃两顿,连碗边都不剩,后人叫这段苦读生活“断齑画粥”。
1917年,毛泽东24岁,正在长沙当师范生。他写给黎锦熙的信里提到:“拟学颜子之箪瓢,与范公之划粥”,毛对范仲淹的苦读佩服到骨子里。能让一个日后开国领袖拿来当榜样的古人,不是简单人物。
范仲淹不是只会读书。他真正的志向,不是做一个会写八股文的官,而是要出人头地,把“朱说”三个字彻底丢掉。
1015年,他终于中了进士,按理说,走上仕途就够了,他没停步,马上回到苏州,要回自己本来的姓氏——范。结果族人挡住门,说他“存心不良”,范仲淹站在族祠前,冷冷回了一句:“我只要还姓范,其他不要。”
就这么一句话,扛回了属于自己的名字。
谁都能忍穷,能扛羞辱的,才是真的狠人。
为民而战,治水安边功中了进士以后,他没有一头扎进京城找关系,而是被派到泰州当个小盐官。换今天说法,就是管个盐仓的基层公务员。没人把这活当回事,出了问题也没人负责,范仲淹一上任,直接摊上一桩麻烦事——海堤坏了。
这不是哪条沟渠塌了,是整个沿海盐田被海水灌了,田地被淹,盐场瘫痪,百姓一夜之间流离失所。当年没人管,年年冲,年年修,年年烂。
范仲淹二话不说,上书请求修海堤,上头压根没搭理他。别人装聋作哑,他直接下乡动手干。
他跑到兴化,当了县令,带着几万人开始筑堤,挖泥,搬石,指挥调度都要管。三年下来,人黑瘦了一圈,堤却真修成了。百姓感激得不得了,把堤叫成“范堤”,这一叫,叫了一千年。
现在江苏泰州,还有这个堤,还叫“范堤”。治水这种事,不出事没人看见,一旦出事全城倒霉,他做的是没人争着干、没人感谢的苦活。
从那以后,朝廷对这个“基层小吏”有了印象。
后来他被调到苏州当知州。治水、筑堤、清田亩,他干得利索,地方太平。
真正让他名震天下的,还不是这些,而是那一场和西夏的较量。
1038年,西夏李元昊造反,边境告急富途证券,宋廷一片混乱。范仲淹当时已经在朝做官,皇帝让他带兵去延州抗敌,文官带兵,历代难成。
很多人以为他会推脱,没想到,他干脆答应了,骑上马就去了西北前线。
边地兵心涣散,军纪废弛,范仲淹干了三件事。
第一,筑城防守。他主张“久守为上”,坚壁清野,稳住阵脚;
第二,操练新兵。他整顿兵制,选拔精兵,像种世衡、狄青这样的猛将都是他提拔的;
第三,稳定军心。他把士兵家属接到军中安置,边民安居,士兵无后顾之忧。
结果是,李元昊屡攻不下,西夏节节败退。
那时候边塞流行一句顺口溜:
“军中有一韩,西贼闻之心胆寒;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
范仲淹是文人,这种军中传言对他而言是莫大的认可。几十年后,毛泽东回顾中国历史人物时,专门提到范仲淹:文武双全,能写千言,也能带兵打仗。
后人以为范仲淹是靠“忧乐”成名,其实错了,他的根本,是“肯干事,能扛事”。一个文人,扛起边疆、治好水患、扛得住冷眼,这才是真本事。
庆历新政,忧乐天下心范仲淹在边关打出威名,按理说可以封功晋爵、安享清闲,他却主动请缨回朝。为啥?不是为了升官,而是为了整顿这个已经烂透的官场。
当时的宋朝看上去歌舞升平,其实内部空心化得厉害,冗官太多,税收不足,兵不知兵,吏不知法。皇帝仁宗无力,宰相多是和稀泥,没人敢动真格。
1043年,仁宗终于下决心搞改革,范仲淹被召回京城,任枢密副使,相当于政坛二把手。
他没客气,上任第一天就拉了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几个硬茬,联合写了一篇奏章,递上十条改革意见。这篇奏章史称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是宋代政改第一文件。
里面点名痛批官员懒政、科举弄虚作假、兵役压垮百姓、法纪形同虚设,还提出要:
明确官员升降标准; 压制靠裙带上位的侥幸之徒; 改革贡举制度,选真正的人才; 减轻百姓负担,让老百姓喘口气。朝堂一下炸了锅。
有人喊他是“道学家”,“不近人情”,有人咬牙切齿:“他才回来几天,就把我们这些老油条全骂了。”
可范仲淹动都不动,他把几个顽固守旧派直接罢了官。富弼有点坐不住,跑来劝他:“你这一笔下去,是几家人哭啊。”
范仲淹只回了一句:“一家哭,好过一路哭。”
这不是说大话,范仲淹改革动了很多人的奶酪,被排挤、被诬陷是意料中事。短短一年,新政失败,他被贬到了邓州当通判,一脚踢出京城。
就在这一年,他写下了最有名的一篇文章《岳阳楼记》。
他的好友滕子京被贬到岳州,修完岳阳楼,托他写篇文章。
他没写风花雪月,也没写高楼美景,写的全是“忧”与“乐”。
写这篇文章时,他已经知道,新政失败,自己再也回不到中枢。
可他没抱怨一句,他说得明白: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
这不是给读者写的,是他对自己的交代。
一个人一辈子都在扛事、担事、为别人考虑,凭啥不值得后人景仰?
范氏义庄,德泽千年长政坛失意,回乡养老,这是多数大臣的结局,范仲淹也回了苏州,但他没把自己当闲人。
他干了件让后世惊掉下巴的事,拿出自己田产上千亩,成立了一个“义庄”。
这是什么概念?
不是捐给国家,也不是做面子工程,而是建立一整套制度,规定怎么救助家族中读不起书的孩子、怎么资助失业落难的亲戚、怎么发放义米给孤寡老弱。
一切写得清清楚楚,像是写公务文件,管理、审计、监督机制都有。
从1050年开始,这个“范氏义庄”就运作起来了,八百年没停。比宋朝长命,比元朝长命,比明朝还长命。
到清末民初,这个义庄还在继续分粮施米,为族人付学费。现代中国慈善史研究者都公认,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制度化的民间慈善组织。
如今,苏州景范中学的旧址,就是当年范氏义庄所在。
他没为自己修庙,没留子孙金银,只留下规矩和影响力。
更厉害的是,他的精神不是关起门来传的,而是被整个时代传下来了。
延安窑洞里,刘少奇给党员上课,说:“共产党人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。”毛泽东在韶山祖坟前,低头念了句: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
这句话,不是拿来当口号用的,是范仲淹用整个人生践行的。
他没留下兵权,也没留下封地,但留下了一个时代最沉重的一句话。
谁能想到,一个从小被赶出族门的弃儿富途证券,一个穷得只能吃稀粥的学子,凭一支笔、一颗心、一身骨气,撑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。
发布于:山东省九五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